

国庆之前,央视播出了《辉煌中国》纪录片,第一集《圆梦工程》以港珠澳大桥为入口,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宏伟蓝图。“对于这个东方大国来说,这55公里连接的,不仅仅是粤港澳三地,未来因它而形成的5.6万平方公里区域,将是继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之后,世界经济版图上又一个闪耀的经济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以来热度持续攀升。作为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以珠江至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发展,并辐射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大格局。而如今,篇章刚刚开启。
又一国家级战略的诞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此后,一系列调研、部署、编制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制定该项规划的牵头单位,“两会”一结束就发出公告,面向社会开展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建言献策活动;广东省积极参与其中,在其4月公布的《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格局。直至7月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很多人看来,粤港澳大湾区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重量级的区域经济战略。但其实,它的酝酿由来已久。
早在2009年,《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就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落实跨界地区合作。2012年,广东省政府公布的《广东海洋经济地图》首次明确提出,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将划定“六湾区一半岛”,打破行政界线,以湾区为单位进行发展。2013年,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在谋划当年工作时,首次提出发展“湾区经济”,并于次年将这一概念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直至此时,粤港澳大湾区仍停留在以年为单位,以地区自发构想为主要形式的缓慢推进中。不过,变化已经在悄悄发生。
“亚投行之父”郑新立,2014年受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托做了一个课题,得出结论“打造世界一流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并完全应当上升为国家战略”。他将这份建议报送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其后又上升到国务院。郑新立是发出此建议的专家之一,但并不是唯一。事实上,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性越发显著。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大湾区”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家公开文件中。此后至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度明显加快,各类国家文件中开始频繁出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字眼,并对其委以重任。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自2016年开始也频繁调研该区域——一切动作似乎都预示着将有大动作。
如今谜底揭晓,粤港澳大湾区也即将在年内迎来首份国家级规划,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继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之后,粤港澳大湾区或将成为第四大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盔甲与软肋
湾区,是面向大海,由一个和若干个海湾及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由于地理和资源等因素带来的便利性、集聚性和开放性,湾区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适宜地区。全球范围内,公认发展比较成熟的湾区有纽约、旧金山和东京。这三大湾区均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因此吸引了众多人口和产业集聚。
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和GDP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国际三大湾区,从面积看甚至达到三大湾区均值的2倍有余。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美国独立智库米尔肯研究所研究院黄华跃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后将成为湾区中最大的区域经济体系。
事实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与世界三大著名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除了空间辽阔、人口众多之外,还具有特殊的比较优势。包括:地理纬度条件好,自然禀赋优越;城市体系完整,已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区位交通便捷,经济枢纽基础扎实;经济实力雄厚,产业体系完备;高端要素集聚度高,创新力较强;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好,国际化程度高;试验功能平台众多,战略叠加优势明显等。这些比较优势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是为其未来发展保驾护航的坚强盔甲。
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软肋也较为明显。“与世界三大著名湾区相比,这里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要整合不容易。”黄华跃认为,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提了多年,直至“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才有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看得更为透彻。他在《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所在。这一格局带来了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导致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充分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
“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多种实验或试验基地等特殊元素,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打造一个共同认可并积极遵守的体制?在最基本的层面应该做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魄力和智慧。”范恒山表示。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粤港澳大湾区的“9+2”格局中,包括珠江三角洲城市群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些城市中不乏经济实力相当、发展速度趋近的城市,因此长期以来,都存在核心城市之争。
此次规划发布之前,关于核心城市花落谁家的问题,讨论络绎不绝。有人认为,广州优势明显,尤其在硬件建设上,广州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已经稳居珠三角最大、最高效的交通枢纽;也有人认为,深圳态度积极,发展潜力更大。黄华跃就非常看好深圳,认为深圳创新性非常强,制约因素较少。除此之外,香港也是一个积累深厚的国际化城市,竞争力不可小觑。
然而,从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状况看,从中确定一个核心城市似乎并非必然之事。如东京湾地区主要有东京、横滨、千叶等几个特大城市以及川崎、船桥、君津等工业重镇,其中千叶主攻原料输入,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的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各城市根据自身特点“术业有专攻”,形成协同优势。再如旧金山湾区,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西三个大城市共同打造了一个“科技湾区”。
同样,广州、深圳、香港各有优势,香港拥有领先的金融和科技服务业,深圳的创新生态完善,广州拥有强大的高校科研院所力量,且有通达全国乃至全球的交通货运。因此,3个城市可以专注于自身的优势领域,变竞争为协作,才能形成“共振”。
范恒山指出,应从发展定位出发来考虑,既要发挥出粤港澳大湾区及其所有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又要立足城市群资源要素高度集中、运行机制能动高效等条件,充分发挥其引领、支撑、辐射带动功能。
事实上,“一带一路”,就是眼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关键支点。从空间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从时间上看,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进度明显加快,将其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打造的意图较为明显。
比起竞争谁是核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整体的机遇更为宏大。与“一带一路”相配合,它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为契机,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和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7个方面的合作将徐徐展开。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消息显示,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作重点是:研究推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制;会同粤港澳三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制定年度工作要点;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一步发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在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方面的试点示范作用。
 领命出征!内地援港抗疫专家组抵港 4人均来自广东
领命出征!内地援港抗疫专家组抵港 4人均来自广东  广州南站迎节后返程高峰 10条夜班公交线路通宵“兜底”
广州南站迎节后返程高峰 10条夜班公交线路通宵“兜底”  南海之滨秒变冰天雪地——探秘深圳最大冰雪室内场馆
南海之滨秒变冰天雪地——探秘深圳最大冰雪室内场馆 再见,广州王府井百货
再见,广州王府井百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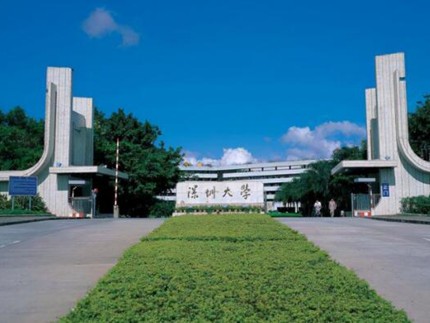 中科院院士毛军发出任深圳大学校长
中科院院士毛军发出任深圳大学校长  短信邀请 自助秒批 测试提速 深圳数字人民币加速落地
短信邀请 自助秒批 测试提速 深圳数字人民币加速落地